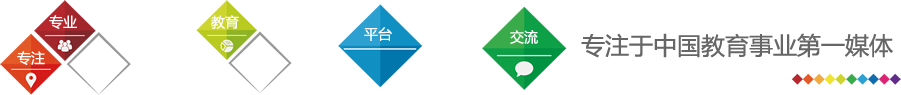我们年轻的时候
当过兵,你的人生因此不同
当过兵,你的回忆甘之如饴
08宣传队照片故事
秋千絮语:今天的“封面故事”来自遥远的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的人们如何生活?如何思想?又如何为自己留下青春的影像?百望山下这篇沉甸甸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视角。
每个人终归都有老去的一天。当我们站在未来的某一时点回望今天,是否也能够像08宣传队的这些前辈一样,赞颂曾经的生活、赞美情同手足的战友?
为了保留四十年前照片原汁原味的感觉,本期所有图片仅仅做了一些必要的剪裁。一些照片的折损与污斑也原封未动。
下面,就让我们欣赏08宣传队那些青春的容颜,那些快乐的身影,那些收藏在内心深处的温暖故事吧。
(本期刊登的所有照片,均葆有其原本的历史面貌。特此提示。)
在公众号里看到燕子(《摄影是一种修行》)和沙泓(《用镜头记录永恒》)刊发的那些精致、高妙的摄影作品,感慨之余,不由得想起自己初学摄影时的情形。
那时比不得现在,既没见过长枪短炮,又受到胶片短缺的限制。一个120胶卷只能拍区区12张,每一次按下快门,总免不了考虑一下弹仓里还剩多少子弹。当然,局限也不都是坏事,局限有时会把你的想象逼向极致。但如果你连一架照相机都弄不到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私人拥有一架照相机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尤其在部队,为防止偷听敌台,个人连收音机都不能有,更别说挎一架照相机招摇过市了。去照相馆照一张相片,是当时绝大多数人存留影像的唯一方式。下面,就先看一张在照相馆拍的战友合影吧。

图一:这是十七岁时一个星期天,和两位战友结伴去连云港海州曙光照相馆照的相片。那时心无落尘,每一天的太阳都新鲜透明。前排右边便是本人。
我所在的部队,营房在山东临沂,连年驻扎江苏连云港国防施工。入伍伊始,我便被选入了宣传队。说实话,那时的我浑身上下找不出一丁点艺术细胞。此前唯一一次和艺术沾边,还是在复课闹革命的十一学校。因心仪的一个女生进了学校文艺团,我也自告奋勇跟了进去。进去也是闲人一个。闲来无聊便抄起一面铜锣,玩命敲了一下午。结果转天学校就找到家里,说我把学校唯一一面铜锣敲裂了,要照价赔偿。钱肯定是给了人家。赔进去的,是我们姐弟仨那个月的饭菜钱。
我们宣传队有三个男兵班一个女兵班,再加上队部的正副队长指导员外加一名政治处干事,统共30来人。最初,自命毛泽东思想战士业余宣传队,后来简化了,就叫08宣传队。宣传队多数时候演些小节目,比如数来宝、相声、京韵大鼓、天津时调,也排演过样板戏里的《红灯记》、《海港》片段。最火的时候,还排演过全本革命现代京剧《红嫂》(现代京剧《红嫂》后来被改编成舞剧《沂蒙颂》,也成了样板戏)。

图二:摆拍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典型形象,上了报纸。照片中是我的老搭档中航和我。
为了摆拍这张照片,也真难为了当年那位摄影记者。组织来这么多老的小的“观众”不说,还要布灯,还要用小板凳摆出高低错落。细心的人留意前排正中背身坐的那个观众穿的脏衣服,就知道这个文艺演出演到了怎样的“田间炕头”。
我们平时上山下乡演出,场地确实简陋。但再简陋,好歹也有个土台子之类的地方。像这样生造出来的演出场面,一扬快板,眼瞅着就打到了观众脸,这种事真还没遇到过。不过,假模假式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照片既然上了报纸,我们这些假典型自然也难辞其咎。
眼看着快到20岁的时候,终于等来了摆弄照相机的机会。
那是197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重拍《南征北战》,我所在的部队奉命配合电影拍摄。我们宣传队的男兵女兵,也因此有机会在电影里小露尖尖角。虽说不过是些师长警卫员、民兵队员、国民党匪兵之类的群众角色,但毕竟在电影里你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你,为此津津乐道。
这部假得一塌糊涂的电影没上映多久,很快就伴随着文革的结束泥牛入海。40多年过去,这部电影最后的忠实观众,笃定要到08宣传队或者认识他们的人中去找了。只不过,这些忠实观众可能并非醉心电影本身,而是从中寻找自己的青春印记。


图三、四:上一张是大沙河边送别一场戏的拍摄现场。下一张照片里的三个雄赳赳的战士,便是我们08宣传队三位战友扮演师长警卫员的试妆照(别误会,这些照片没一张是我拍的)
还记得,新《南征北张》拍摄期间,北影厂和部队联合组织慰问演出。主要演员表上的王尚信、张连文、鲁非、张勇手、田宝富、白志迪、胡朋,以及主要演员表上没有的葛存壮,又是演小品,又是当指挥,各展所长。我们08宣传队的相声、数来宝、器乐合奏,也悉数登场,同台献艺。
成荫导演坐在台下第一排看演出,笑得前仰后合。次日一大早,个头不高的成荫导演带着一帮人,直奔我们宿舍。看那意思,肯定是来挑选演员。但那时候,宣传队不少男兵鼻子下面还是没剃过的汗毛。加之部队的伙食每人每天四毛五,没太多油水,20岁的人了,脸还没长开。上台演出,画上重油彩妆,灯光一照,显得高大成熟。但卸了妆,个个枯黄干瘦,一人一张娃娃脸。成荫导演看过来看过去,最终悻悻而去。
成荫没看上我们,我却看上了大摄影师聂晶。在电影拍摄现场,一天天地看他坐在高高的升降机上抱着摄影机,威风八面。尤其摄影机一开起来,马达“哒哒哒”一串脆响,甭提多悦耳动听了。虽说我蒙混过关,群众演员让我当了一溜够——穿上农民服装是游击队,穿上国民党军装是匪兵,换上解放军军装又成了师长警卫员。但真正让我心痒手痒的,还是傻呆呆地望着聂晶坐在升降机上,摇拍远处连绵不断的烟火。
总说天上不会掉馅饼,没多久,馅饼真还砸到了我的脑袋上。宣传队卢干事不知打哪弄来一架照相机,摆弄来摆弄去,机箱盖都打不开。卢干事举着相机四处找帮手,我奓着胆子接了过来。那是一架国产海鸥120相机。一摸到相机冰凉的铁壳子,我差点没乐掉了下巴。

图五:家父七十年初拍摄的天安门晨曦
摆弄照相机,说到底还是得益于家庭熏陶。家父喜爱摄影。但我15岁出门远行前,他还没来及悉心传授。不过,从襁褓里就开始当家父的模特,一月月、一年年看下来,傻子也悟出一点门道了。虽说端起那架海鸥120的时候,对构图、景深这些高奥的问题还混混沌沌,但光圈与速度的关系,调整焦点,以及胶卷的定数,灯光片还是日光片等基本要领,则已成竹在胸。
这不,平生第一个胶卷,让我抓拍到一个欢乐的瞬间。

图六:快乐的一群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南征北战》电影临时搭的景——将军庙火车站。画面中快活的一群,便是我们08宣传队的一众男兵。
那时胶卷奇贵。当兵头一年每月津贴六元,到第四年每月升到十元。一月津贴依然买不了一个胶卷。市面上,有时会有简易包装的胶卷出售。那是厂家将回收的胶卷轴和包皮,再次使用。这种胶卷弄不好边缘会走光。可部队又没处去找安装胶卷的暗袋。为保万无一失,只好找一条厚裤子,扎住裤腰,将相机和胶卷放在其中,两只手从裤腿里伸进去,再让旁人用棉被把我严严实实包裹起来。盲装胶卷一装一身汗,好在一次也没有失手。
再说说照相机。当兵当到第五个年头,也就是1974年的下半年,政治氛围大为缓和。回家探亲时,将家父那架捷克产的120相机带到部队。那阵子,只要不大肆声张,拍拍照片,已没人拿你当间谍特务。这一来,这架成像不错的相机便成了我最初实习的忠实伴侣。

图七:这张照片便是那架捷克相机拍的。尽管背景只是营房边的一片菜地,但片中我们08宣传队的战友,或成熟、或幼稚;或刚烈、或绵柔;或豪情万丈、或耐得寂寞;每个人的心性都袒露无疑。40多年过去,每次翻看这张照片,一个个活脱脱犹在胸臆之间
在我少年的印象中,捷克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因为从小坐的圆头圆脑的公共汽车,就是捷克产的斯柯达。而家父早年买下的那架120相机,也是捷克产品。我至今清楚记得,那架相机的最快速度是800分之一秒。机械装置达到这个速度,已属不易。只可惜,这架伴随我长大的捷克相机,与我作伴时间却十分短暂。一次带着它去长城拍照,半道上被贼偷去。丢相机的感觉,比失恋有过之无不及,好些日子昏天黑地。
前些时候忽发奇想,上网转转,别说,还真有人出售我丢的那款捷克相机。只是,过了40年再从图片上见到它,它也老了,面色无光,满脸褶皱。问问价,也要几千上万,姑且作罢。
我们08宣传队的一众战友,聚在一起是一捧晶莹剔透的珍珠。分开了,百里千里、山山水水地隔着,一颗颗依然光可鉴人。
远了不说,就晒晒同在京城的几位战友吧。当年胶卷稀缺,每一张都不知掂量多久才按下快门。好在,不多的几张习作,可以带我们穿越时空,重返那个青春年少的时候。

图八:三秋
先说这一张吧。主人的名字好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老兄大名正是“三秋”。这张照片拍的是三秋从宣传队去了通讯排,坐在交换机前摆了个轻松惬意的姿势。其实,三秋这样的通讯兵,平日里抱着线拐子训练,呼哧带喘一跑几里地,累个贼死。
阴差阳错,这张照片拍出来40多年,愣没交到三秋手上。不难想见,前些日子三秋在微信群里头一次见他40年前这副俊俏的模样,该是何等心情。
三秋复员回北京后,当了水官。虽说职务比芝麻粒儿大不了多少,但责任却比山大。不信?大北京城,断一天水你试试。要不,前两年习主席视察北京自来水,怎么会和他握手呢。

图九:鸽子王
再看看我的第二位战友。“鸽子王”是后来才有的绰号。
鸽子王当年在宣传队负责灯光音响。如果我没记错,应该还拉过大幕。至于为什么我会给他拍一张身穿白大褂、手握《新医学》杂志的照片,具体情形想不起来了。也许,老兄当年心中确有如此远大的志向;也许,只是因为一时抓挠不着别的行头,临时抱佛脚。不管咋着,这位老兄复员回京,老本行叫他发扬光大,从无线电到系统集成,计算机买卖做得风生水起。
有时候,人心里面的事,搁谁都揣摩不清。前些年聚到一起,才知他又新添了爱好,养鸽子。战友们喊他一声“鸽子王”,绝非给他戴高帽。他养的信鸽数量惊人不说,单他手里那几羽来自国外、出身高贵的国际比赛冠军鸽,就让他在国内信鸽界有了一号。

图十:叶大夫
最后再说说叶大夫。原本,叶大夫是那种头发梢上都挂着音符的大才。次中音号、二胡、小提琴、柳琴……每样乐器到了他手里,一准玩出花来。只可惜,08宣传队条件所限,委屈了他这块材料。记得有一次,叶大夫全然不顾部队作息时间,躲在一间杂物室拉小提琴。结果被前来视察的领导逮了个正着。领导有话“满天的蜘蛛网,满地的箩卜皮,还拉着什么小夜曲……”可怜啊,宣传队所有小提琴一律封存。
叶大夫后来复员回武汉,弃艺从医。先在湖北中医药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接着远赴东瀛,在日本爱知医科大学拿了一个医学博士学位。有时候,人心里的喜欢,躲着闪着,怕沾上了伤心,可喜欢的事情偏还来招惹你。要不然,怎么叶大夫在名古屋开一家小餐馆,大指挥小泽征尔也会登门做客呢。
眼下,叶大夫正身穿白大褂,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北京平心堂中医专家诊室正襟危坐。据官方介绍,叶大夫擅长中医内科。诸如妇科疑难杂症,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疾病,帕金森病等等。前些年,挂他一个号,要三百块,不知近来是否水涨船高。
值得庆幸的是,宣传队的战友大都调养得当,尚不劳叶大夫操心伤神。何况,战友们还有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每次聚会,排队请叶大夫搭脉(叶大夫将号脉谓之“搭脉”,倒也十分形象),不已成了保留节目么。
最后,还要絮叨絮叨文章开头那张三人合影。照片中的站立者,在群里昵称“亦舟”。照片前排左边那位,则已经失去联系40年。要说,都居住在北京这座城市里,找个有名有姓的人不应当这么困难。但实际情况却是,人海茫茫,查询无处。
有时候一人枯坐,不免胡思乱想,莫非我这兄弟已遁入空门,剃发当了和尚?前些时日,还有战友提议,是不是该上倪萍主持的寻人节目“等着我”。
这篇拙作的结尾,看来有必要做一则寻人启事——
寻08宣传队战友史刚。
望你得到此信,即刻归队。战友们念叨了你这么些年,你就没打两个喷嚏么?
恳望知道我这位兄弟下落的朋友,传个话到下面这个邮箱:
qianniangushi@yeah.net
在此,还要敬请宅心仁厚的朋友们帮忙转发此文。说不定,我那失散40年的兄弟真还就看到了您转的文章呢。